优质回答:
第二节 亚奶

时光是一个很淘气的孩子,再后来,她不知把亚奶藏到了哪里。当我走进那条小村的时候,只有几棵杨桃树在落寞生长着。
听老一辈的人说(说老一辈有点夸大其词,只不过是我爸的同辈),我们的祖先本不在现在的小村里。大概是一百年前,太祖公带着他的家眷撑着疍家婆船沿着大江顺流而下,举家迁徙到大江边。然后再过十几二十年也就是大约在九十多年前,太祖公再带着他的七个儿子搬到了我们现在住的小村。就这样,我的祖先们在大江边安家落户,开垦荒地,然后开枝散叶,经过几代的生息繁衍,由十几个人变成了现在的一百多号人,并且在在鸟洲也有了我们的村号相里村。
哦,原来如此。每次听到这个小村的故事,我都会不由得想起百年孤独这个词。
按记载,爷爷那一辈是小村的开村史的第二代人物。再后来,爷爷那一辈只剩下亚奶一人。再再后来,亚奶也到了一个好远的地方,去做了神仙。
亚奶是村里年龄最大,辈分最高的老人。正因为这样,那些后辈怎么称呼她便在讨论好多年了。那时候我们的阿泰六爹很亲切地叫她六婶,我妈叫她六奶,我当然叫她亚奶,和我同辈的叫她六叔婆,我堂侄叫她亚祖。而小堂侄一辈的人在村里也大有人在,但他们怎么称呼她,则是个问题了。可惜晚爹不在了,要不问问他可能会知的,他是最懂礼节的了。所以有人跑来问亚奶该怎样称呼她,亚奶说怎么叫也是一句而已,直呼其名也行。当然,从没有人对她直呼其名,大多数人叫她六婆祖。
最令我奇怪的是,亚奶居然有名字,而且还是单名,姓李,名卿,全名李卿。亚奶出生于1916年,那一年搞了场护国运动,袁世凯下台,这说明了自辛亥革命后任何人在中国想称皇帝都是徒劳的。如果我一时忘了亚奶的年龄,但袁世凯称帝失败是哪一年却记得,所以很容易就推算出亚奶的岁数。后来我翻日历又知道1916年是龙年,便告诉亚奶说她是属龙的。她不信,说龙是最尊贵的,只有那些大官宦的人才会属龙。幸好我没说我是属鼠的。
按常理来说,亚奶凭着她的辈分高,资格老,孙子的名字该由她来起才对。但我和两个弟弟的名字是由婆哺——一个巫婆起的。说起婆哺,她可是大有来头,亚奶在文革那十多年(也就是我们村里人所说的搞运动的那些年)和她结下深厚的友谊。那时候婆哺不能公开搞革命。错了,不能叫革命,搞迷信,好像叫迷信也不怎么恰当。反正就是这样子的,婆哺躲在亚奶的小屋里,晚上和亚奶同床共寝,白天给好多女人传道受业解惑。
也正因为这样,亚奶的两个儿子我爸和三爹才能娶到老婆。但是婆哺说我爸和我妈才是她做的媒人,三爹和三奶不是她做媒人的,是华光师祖做的媒人。
再说回名字吧。婆哺除了给我爸和我妈做媒人外还负责给我们姐弟们起名字。所以我才有了这个这么抽象的名字,好多人都说我的名字像个男的好有气势也很爱国。其实这纯属一个误会,我想婆哺当初给我起名字的时候是出于这样的考虑,契华光,所以就有了个华字(在鸟洲,好多人的名字都有个华字)。而我的生辰八字可能缺些金木水火土呀什么东东的另一个字需要个月字旁才吉利,我想应该是这样的。后来我还知道名字只是一个符号而已,所以现在我有了好多个名字,不同的人对我有不同的叫法。不过好多时候我都觉得我应该是叫相里虫虫。
每次在外婆家见到婆哺,她都会和我说起亚奶,她说亚奶身上有一种鸟洲的一般女人所没有的特质。她年青(又可能是中年)的时候一年到头都不怕冷只穿一件衫,她的床上也没棉胎长年都是只盖一床被单。她的四个儿子也从不管她的生活起居的还动不动就对她凶就我爸中厚一些没骂过她,后来婆哺实在看不过去了就提醒了一下下她的儿子们,亚奶这才有了一床被胎。不过她又说亚奶确实是个大好人,不管是谁来了,只要家里还有一只鸡她都会宰来煮饭待客(在这里,请注意这个饭字,那时候鸟洲的人都是吃粥的)。
怎么说了半天还没说回起名字啊。现在说吧,在我们的家族中,除了我三姐弟的名字不是亚奶起的外,其他的孙子的几乎是她起的。她给我大堂妹起名叫观娣,意为观音大士给洋叔的下一个孩子送来一个男丁。但洋婶下一个生的也是女的。这回亚奶就不叫她什么娣了,而给她起个名字叫康娇,认康王大帝作干爹,容貌比亚娇还美。亚奶说亚娇亚凤是最美的,因为她不知道中国还有西施杨贵妃。然而这姐妹俩从来都不承认她们的名字,大姐叫向日葵,小妹叫柠檬。如果有谁叫亚檬做康娇一定被她骂得体无完肤,娇我的娇,你才娇。我们都叫她亚檬,不叫她康娇。亚檬长大后果如亚奶所希望的有亚娇亚凤美。
亚奶给她的第一个曾孙起名叫上官,希望他长大后做大官,好像她还不知道科举取士在中国废除了已近百年。不过堂嫂觉得官字有点俗,就改作观,后来入户口及读书再按族谱里的第二十三世字起个族名。所以亚奶常感叹,给那些人起的名字好好的,可他们的老妈却总是再取别的名字。说真的,对于亚奶起的名字我真的不敢恭维。她起的名字多带个娣字,可见她认为女孩是不该有自己的名字的,起名是为她小弟服务的,虽然她不重男轻女,但祖传香火这一观念在她看来是根深蒂固的。
我从未见过爷爷,但开始认识亚奶好像是四五岁的时候,那时我和向日葵鱼腥草跟她睡。然后我对我们说亚奶的肉好软好喜欢摸。但我妈却说老人的肉会吸小孩的血叫我不要再和亚奶睡了。不过洋婶却有另一个版本,她这样对我妈说,她们是女的,管它呢,让她们跟她睡吧要不你哪有处给她们睡?我们的儿子就不能让他们跟她睡。那时我还是个很小的小朋友,大人们的话我不懂。我对我妈的话半疑半信,但并不害怕。当然后来我和向日葵还是常常跟亚奶睡。
现在我也不知道我是否长大了,不过再来看我妈和洋婶的那一段对话却懂了。虽然我明白我妈的用意,但却有点心酸。算起来,那时亚奶已有七十多岁了,中国古语有云,人生自古七十古来稀,有些事迟早要发生的。但那时亚奶给我的感觉是个年青的奶,我并不知道她的年龄,而且她人很好。
反正我很喜欢跟亚奶睡。后来大伯盖了房子,亚奶有了一个房间还有一张大床。我和向日葵一有机会就会跑去和她睡。我们最喜欢在睡觉之前和她聊天,有时还会叫她讲故事。
不过她给我讲的故事说来说去就那么几个老掉牙的,而且是有好多个版本的。现在我还记得那些故事的内容,有个是“山人雄”(鸟语,相当于普通话的“吃人兽”),有个是“公道主”的(一个佛教故事),还有一个应该是布谷鸟。布谷鸟在鸟洲叫“家婆心毒鸟”,这是亚奶告诉我的。她说那鸟是一个“新妇”(鸟语,相当于普通话的儿媳妇)变的。从前有个恶家婆对她的新妇百般凌辱,后来那只新妇受不了折磨便跳井自尽了,然后变成了一只鸟。那鸟就成日发出“家婆心毒,家婆心毒”的叫声。那个故事被亚奶用鸟语讲得惟妙惟肖,那句家婆心毒我至今仍记忆犹新。
现在想来,真佩服亚奶的勇气,早已身为别人家婆的她居然可以如此坦然地给我讲家婆心毒的故事。可是好多年之后,我突然想到另一个问题。可能布谷鸟说的不是“家婆心毒家婆心毒”,而是“新妇心毒新妇心毒”。在鸟语里,家婆新妇谐音,布谷鸟又吐词不清,至于布谷鸟说的是什么,也只有布谷鸟才知道。
另外,亚奶还给我讲过一个包脚女人的故事。原来那个包脚时代的女人除了小脚走路不便外,还天天都要在头上包一条头巾,就像福建的那些惠安妇一样。所以那些包脚的女人每天都要她老公抱她到灶边,然后再淘好米放好水把柴抱到她身边。她只要抱着个孩子乖乖地呆在灶边生火煮粥就行了,如果粥熟了话她也不能把那粥抬回家的,要等她老公来抬回家。又因为那些包脚的女人头上天天都包着一条头巾,不怎么看得清人有时也会认错老公。如晚上在屋外乘凉那个女人困了就拉着她老公说,“阿哥,回去睡觉吧。”谁知她拉的是坐在她老公旁边的小叔。于是她老公就骂她,“你嘅只癫婆,我在几呢。一烟筒就打死你。”
还有一个包脚婆认错老公故事的版本是这样的。以前我们这边的人都是过渡去趁圩的,可是一年中就有那么一两个时节河水断流撑不了船,人们就下水走过河去的。可是这些头上包着条头巾的包脚的女人行动不便只能在河边扯着嗓子喊,“阿哥——喂——快来咩我过去啊——”于是就有一个男人跑过来对她说,“哥我的哥,我只嘅啦,癫婆。”原来这个男人是她老公来的,他看到这个小脚女人出去就跟在她后面看着她。
还有另一个版本的包脚女人过河的故事情节是这样的。这回背她过河的不是她老公了,而是一个年轻的小伙子。后来到了河中央的时候,这个小脚女人趾高气扬趴在那个小伙子的背上说,“真系有钱使得鬼推磨啊,果边推来喏边磨。你睇亚姐有钱就得喊你哋果帮后生仔在果边江咩到喏边江……”她话还没说完就给那个小伙子给甩到河里去,“你冇系讲有钱使得鬼推磨吗?加下就俾你在水里头慢慢磨,阿哥今日心情冇爽你嘅钱稳鬼来赚。”
亚奶还给我讲过那个疍家婆的故事,她说那些疍家婆会晕岸,在岸上只要一看到那些女人走路一晃一晃就知她是疍家婆来的。而那些疍家仔就会在脖子上挂个葫芦如果他掉到河里的时候那只葫芦就会在水里一漂一漂的,人们就知道救他起来。
长大后,我才知道亚奶讲的故事是很有哲理的。
我敢说亚奶绝对是位伟大的母亲。亚奶在生洋叔的时候在村里也曾被传过一段时间的。那时,大姑妈已生了一个孩子,所以传说中的外甥大过舅是真的。但最有说法的还是三姑妈,那时她才上了一年学,可洋叔的出现却使她不得不辍学回家带弟弟。直到现在说起这事她还埋怨亚奶不该生洋叔。但亚奶的说法是生孩子这事不是人的意志可以控制的。
亚奶的大儿子,也就是三爹,比其他三个大得多,结婚也就比他的兄弟们要早些,早就分家自己过。后来她中间的两个儿子在同一天结婚(据说这样可以省些酒席钱),待她的小儿子也结婚后,就再次分家,三个儿子各过各的,她也自己过。听我妈说分家的时候我还未出世,所以那二十多年来亚奶都是自己养活自己。
早在十多年前,我们村不知把一块什么地皮卖给了政府,好像每个村民分到了七千多大洋的人口钱。所有的子女都建议她把那几千大洋存入银行,以便必要时用来做用使。对此她言听计从,自己老了也终于有了着落。
钱是存入了银行,但亚奶也是要吃饭的,吃饭就是要钱的。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她的四个儿子只在逢年过节或家里有好菜时才叫她过去吃饭,那样的日子加起来一年可能有六十多天吧,但还有三百天得靠她自食其力。于是又有人建议她把那几千大洋拿出来吃掉算了,管它那么长远的事干嘛呢,那些事由你的儿子们来搞就行了。但亚奶不为所动,她知道这几千大洋是绝不能动的。可能这些年日子好过了些,她的新妇们也劝她把那钱拿出来用,要不跟儿子们吃也行,反正她有四个儿子,去哪也只是添一对筷子。
亚奶说她仍习惯一个人过,自由自在的,想几时食就几时食。那些年很多人在小村周围开了很多废品店,那些店每天都会倒出好些垃圾。亚奶也加入拾荒的队列中拿着个米袋去拾废品,然后攒在一起再把它们卖给盲鸡,一年下来也有个千百十的进帐。我们这些做孙的,一看到有什么可卖钱的东东也会给她留着,那时她就会很高兴地接过我们的东东。当然,有时我也会去她那翻她的东东找些新奇的小玩意儿,有次我从她的废纸堆中翻出一本成语词典和一些小说,见对我有用,她也乐意让我拿去。
她的四个儿子虽然一年到头极少给过她一分钱,只有她的三个女儿有时会这个给她塞三十,那个给她塞五十。当然,她的女儿也老了,没有太多的钱给她,可她有很多外甥女,且都结了婚,都会给她一两百的,相里凌更是经常会给她捎些吃的东东和一些大洋。那么些年来差不多一直是相里凌在照顾她的起居饮食。后来在年节的时候村里一些后生也会给她一些票票。
亚奶不用动她的私钱也能活下去,看来多子多福还是有一定道理的。亚奶虽然是村里年龄最大、辈份最高的老人,可她从不倚老卖老,别人有什么关于习俗的礼节问她,她都会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不过也有人说她是个不怎么理事的人,你别看她活了一把年纪,其实有好多传统的礼数她是不记的,所以你问她那些关于礼节的东东她也不清楚。
亚奶的那些孙子无论男的女的在十多年前绝对是调皮捣蛋的,整天围在她身边吱吱喳喳差点没把她闹个半死,说她的话说叫冇得着落。在我们小时候每逢初一十五她都会到阁楼拜神。一到拜神,我们小孩子最开心,因为拜完神就有东东吃。
所以一知道她要拜神,我们就会早早地跟着她。跟着她去铺儿买经果、糕糖、烧酒、元宝蜡烛小鞭炮等东东,然后主动帮她提到阁楼。一到阁楼我们便开始大闹天宫。阁楼供奉的是华光师祖,他旁边还有两个小将。我们都很好奇华光师祖有三只眼,忍不住对此评头品足一番,有时向日葵还会把华光帝手里握的小剑抽出来玩。这时亚奶就会提醒我们,叫我们不要在细鬼弄大神。
当我们闹倦了,亚奶也就叠好了元宝,摆好了茶酒,摆好了贡品,点好香插好蜡烛。她要拜神了。
我还记得亚奶拜神很有鸟洲风俗特色。她会一边磕头一边口中念念有词。那诵词我现在还依稀记得,开头必定是人望神力,草望春生。在念了一通后再依次念出她的四个儿子的名字,并说明他们是做什么的,请求神灵保佑他们身体健康发财就手。当她向华光帝提完请求时,已经三跪九拜结束了,于是起来烧元宝,放鞭炮,末了,再在元宝盆里倒些烧酒。干完这一切后,她又回来重新三跪九拜称之为还神。她在拜神时要求我们小孩子也拜,说神灵会保佑我们快高长大聪明伶俐。
终于拜完了,我们有东东吃了。亚奶把所有的东东装在塑料袋里准备下楼分给我们,可一下楼我们就像山贼一样冲上去抢她的东东,甚至把塑料袋也扯个稀烂。一看到我们开始抢东东,亚奶就把属三六爹的那一份藏起来。如还余些东东她就把它们放在米缸里,她自己几乎从来不吃的。我们这些孙每次到她那的第一件事就是翻米缸找吃的。她也不十分反对有人翻她的米缸,只是说不要全拿完得留些给别人。后来那些孙子都长大了,再也没有人去翻她的米缸。可她的米缸一直都保存着存放些水果零食的习惯。
除初一十五拜神外,每天早晚亚奶也会到阁楼上香。当抬菩萨出游,村里人集体拜神时她也积极参与。
大约是在读上学的五六年级吧,亚奶常去邻村的观音庙里拜神。然后回来的时候她除了带回了糖果外,有时还有进供米、灵符、清凉油什么的。有一次,亚奶从庙里回来给她的六个孙女一人一条小珠手链。那些手链被我的堂妹们戴了一段时间后便不知所踪了。虽然我一向都不怎么喜欢手饰,那条手链我也没戴,但很是却好好地保存着的,因为她是亚奶送给我的唯一的一个东东。后来在小考中考高考我都把那条手链放在衣袋里,我想在人生的某些关键的时刻让它陪着我。后来,来到了离家千里的大学,在我的行李中自然也少不了这条不起眼的手链。但在那天闲着没事我就把这手链拿出来透透气,那串着珠子的橡皮筋可能由于年久老化断了,珠子一粒一粒地落在桌面上。我珍藏了将近七年的手链变成了二十六粒珠子。我把这二十六珠子小心地放进一个小皮袋里,然后在古城买一条类似的手链,用那橡皮筋把这些珠子重新串了起来。
除了拜神,亚奶也很注重拜祖。每年的二月和八月村里有很多祖忌。一到拜祖那天,亚奶就会叮嘱我妈她们不要先吃饭,要拜祖。在鸟洲的风俗里是祖先吃了再到人吃的。然后她就会提醒新妇们在拜祖要注意的事项。拜祖的饭要堆得冒尖。至于菜肴最好是丰盛些,而且要有咸鱼和豆腐(骗鬼吃豆腐原来是真的)。还有烧香时左手边的香炉也要插三支香,蜡烛也是插在这个香炉的,这和拜神是不同的。还要记得调台(在鸟洲,台就是八仙台),在相里村,平时吃饭台面的纹理是竖着的,但拜祖时就要横着的,叫横台,而且要在它的上位放一条长凳或五把椅子。烧纸钱时不能放反了要不祖宗就收不到了。
七月十四十五是民间的鬼节,在鸟洲给祖先和鬼烧的纸钱特别多,而且还有鬼鞋和花纸(花纸是给阴间的人做衣服用的)。我记得好多年前一到鬼节前夕,亚奶就会叫上我和鱼腥草陪她去十字街买祭祀用的物品。在鸟洲买鬼鞋是很讲究的,一般人家是不能买那种粉红色纸糊的包脚鞋,只能买几对黑色的纸男鞋和黑色的包脚鞋,那是烧给祖公祖婆的,还有一大串小鞋是烧在屋外烧给孤魂野鬼的。到了买鬼鞋的时候她又会叮嘱大伯要记得买花包脚鞋。花包脚鞋是烧给年青时过身的女人的,先伯母不在世的时候才三十多岁。大伯是个办事也算有交代但脾气爆躁的人,他最受不了亚奶的唠叨,他就吼亚奶说他知道该怎么做不用她多事。
一般情况下,买完了鬼鞋,亚奶也会给我和鱼腥草买真鞋。在这一点上她可是毫不忌讳的,她说阴间有阴间的鞋,阳间有阳间的鞋。我最奇怪的是为什么我们的鞋老是在七月十四的时候着坏的呢。再后来,那些年亚奶可能真的老了,她不再买鬼鞋了,至于那些祭祀的事务她就完全交给了她的新妇们。
村里的好多三姑六婆都喜欢和亚奶扯家常。那些大婶大娘总爱说她们的新妇怎样难侍候,对老人又怎样的苛刻。亚奶却很少说新妇的不是。当那些老妇在感叹世风日下人心不古时,亚奶也只说其实都是你看我好我看你好而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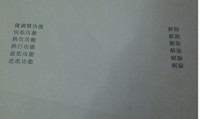


0条大神的评论